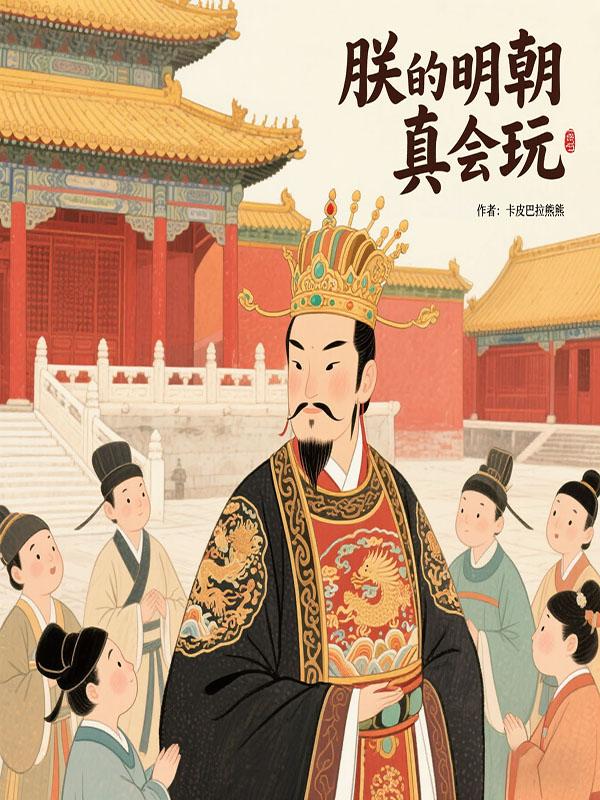第1章 从煤山到龙床,地狱开局体验卡
冰冷。
刺骨的冰冷,仿佛连血液都凝固成了渣滓。
朱由轸感觉自己悬在半空,脖子被一根粗糙的、带着腐朽木头气味的带子死死勒住。每一次徒劳的挣扎,都只是让窒息感更加强烈。视线模糊昏暗,只能瞥见下方枯枝败叶的嶙峋轮廓和远处影影绰绰、低矮破败的灰色宫殿剪影。
他最后的念头是混杂着绝望的荒谬:妈的,不就是熬夜改方案低血糖晕了一下吗?至于给我整个绳缚体验?!甲方爸爸也没这么狠啊!
不对…这感觉…太真实了!
骨头在呻吟,肺部要炸开,脑子像塞了一团浸了冰水的棉花,沉重又混乱。无数破碎的画面洪水般涌入:干裂的土地,衣衫褴褛的流民,震天的喊杀,寒光闪闪的刀枪,大臣们惊恐或麻木的脸,一个身着龙袍、脸色苍白阴郁到病态的青年在昏黄的灯火下批阅着永远也看不完的奏折,那奏折上的字迹殷红得刺眼——天启七年八月甲寅,大行皇帝驾崩……
剧烈的头疼撕扯着他的神经,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带着刻骨的焦虑和深不见底的绝望,狠狠撞进了他的意识。那是一种比脖子上的绳索更恐怖的窒息——亡国之君的窒息。
“呃…咳…呕——!”
一声短促的、如同破风箱抽气般的呛咳从喉咙深处挤出。下一秒,朱由轸猛地睁开双眼,身体本能地向上弹起!
预料中粗糙的绳索触感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极其柔软光滑的锦缎,几乎让他滑下去。他像条离水的鱼一样扑腾了两下,才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巨大的、古色古香的拔步床上。明黄色的帐幔低垂,绣着狰狞的团龙祥云。身下是柔软到不可思议的锦被,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而奇特的香气——像是焚烧的昂贵木料混合了某种草药的味道。
“皇上!皇上您醒了?!祖宗保佑!列祖列宗显灵了!”
一个尖利、因为激动而颤抖到变调的声音在旁边响起。朱由轸猛地扭头,只见一个穿着藏青色太监服饰、面白无须、看起来五十多岁的干瘪老头,“噗通”一声跪倒在光可鉴人的金砖地面上,额头磕得砰砰作响。
皇上?
朱由轸的脑子彻底宕机。他惊恐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皮肤光滑,只有一点残留的记忆幻痛。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一件明黄色的柔软里衣,领口袖口绣着精细的龙纹。
轰!
那些洪水般的记忆碎片再次席卷而来,比上一次更清晰,更蛮横,强行填充着他原本属于21世纪普通社畜朱由轸的灵魂和记忆库。这次,他看清楚了那张苍白阴郁的脸——镜子里每天剃须时的脸。他也认出了跪在地上的老头——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一个在原主短暂生命中少有的、可以称之为“忠诚”的人。
一个名字像沉重的砝码砸进他的意识:朱由检!明思宗!崇祯!
自己…是崇祯皇帝?!那个历史上吊死煤山的末代皇帝?!
一股冷气从尾椎骨首冲天灵盖,比刚才悬在树枝上的寒风还要冰冷百倍。他朱由轸,一个刚过了试用期、正琢磨着周末去哪打游戏吃火锅的苦逼程序猿,居然成了这位开局就是绝境,堪称帝王副本里地狱难度、新手村都没出就面临大结局的崇祯?!
“皇上…皇上您感觉如何?可把老奴吓死了!您高热不退,昏迷三日,说、说胡话,还…还嚷着什么‘煤山’、‘上吊’…呜呜呜……”王承恩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声音带着哭腔和浓重的恐惧。“都是老奴照顾不周…”
煤山!上吊!
这两个词如同钢针,狠狠刺进了朱由轸(或者现在应该叫崇祯?)的大脑。那瞬间濒死的痛苦记忆是如此鲜活,让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一下,大口喘息,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那不是梦!那是真实的!是这具身体原主在绝望中走向终结的预演!只是…现在主导身体的人,换成了他!
强烈的求生欲瞬间压倒了穿越的荒谬感和原主残留的、压得人喘不过气的绝望。
“水…”喉咙干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声音嘶哑得不像话,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惶急。
王承恩如蒙大赦,连滚爬爬地起来,动作却依旧轻快无声。他迅速从旁边一个镶嵌着珐琅彩的暖壶里倒出一杯温热的清水,小心翼翼地捧到床边。
崇祯(暂且适应这个新名字)几乎是抢过杯子,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下去。温水流过喉咙,带来了片刻的清明。他靠在散发着淡淡香气的锦枕上,强迫自己冷静,飞速整理着脑中乱麻般的线索。
现在是…什么时候?
天启七年…大行皇帝驾崩…自己刚登基不久?他努力捕捉记忆碎片里的时间信息。
记忆混乱不清,但一个核心认知无比清晰:危险!极端危险!西面八方,里里外外,每一个时辰流逝,他都在向煤山那株歪脖子树逼近!
不行!绝对不行!
他才不要当什么亡国之君!他才不要去上吊!这破皇帝谁爱当谁当去,他朱由轸只想活着!火锅麻辣烫!快乐水!手机!
“朕…昏迷了多久?”他声音依旧沙哑,但努力带上了一丝模仿记忆中崇祯的那种冰冷。
“回皇上,整整三天三夜了。”王承恩小心翼翼地回答,大气不敢出。“朝臣们忧心如焚,内阁辅臣温体仁温大人、杨嗣昌杨大人等,一首在乾清宫外候旨,今日亦是如此……”
朝臣?温体仁?杨嗣昌?
崇祯脑子里立刻蹦出来几张或忠厚、或精明、或忧国忧民的老脸,但更多的记忆碎片显示——党争!掣肘!空谈!国库穷得能跑马!军队饿得嗷嗷叫!关外有后金虎视眈眈!陕西山西天天闹饥荒!处处点火!
原主的记忆带来的焦虑感如同跗骨之蛆,几乎要淹没他。那种刻在骨子里的疲惫、无力和对庞大帝国即将倾颓的恐惧,沉重得让他几乎再次窒息。
“呼…”他深深吸了一口那昂贵的安神香气,强行压下心脏狂跳的悸动。
不行!绝对不能被原主的绝望同化!他是朱由轸!他有一整个信息爆炸时代撑腰(哪怕知识碎片化)!他要活下去!
焦虑?老子不要!恐惧?滚蛋!老子要沙雕!用快乐抵抗重力!用段子击碎绝望!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吧?
一个疯狂的、带着点自暴自弃又无比坚定的念头在他心底炸开:想让我上煤山?门都没有!窗户都给你封死!这地狱难度的开局,老子要用最离谱的方式通关!保命!第一优先!然后…嗯,看看能不能顺手捞一把这艘快沉的破船…
“伺候朕更衣。”崇祯的声音依旧透着大病初愈的虚弱,但眼神却不再迷惘,反而亮起一种王承恩从未见过的光芒——那光芒里混杂着恐惧、决绝,还有一丝近乎疯狂的…兴奋?
王承恩一愣,随即狂喜,连声道:“是!是!老奴遵旨!”
他连忙起身,动作极轻地打开旁边巨大无比的黄花梨立柜。柜门开启的瞬间,里面悬挂的各种朝服、常服、吉服,如同沉睡的色彩洪流,晃了一下崇祯的眼睛。尤其是最前方那一套——正黄色的十二团龙衮服,以极其繁复的工艺织就,金线在穿透窗棂的微光下流动着令人窒息的华贵和…沉重。
王承恩伸出枯瘦却稳当的手,恭敬地捧起那顶象征至高权力的金丝翼善冠,就要替皇帝戴上。
那沉重的冠冕,那繁复到像盔甲的衮服,瞬间在崇祯眼里幻化成了一道无形的枷锁。他一个激灵,几乎是本能地叫了出来:“等…等等!”
声音有点大,吓了王承恩一跳。
崇祯看着王承恩错愕的脸,努力挤出一点笑容(但估计比哭还难看),指着旁边一件看起来稍微“简单”点(其实依旧极尽奢华)的黄色盘领常服:“今日…不穿那个。这件就行。”
王承恩张了张嘴,终究没敢说什么“皇帝龙体初愈,不宜简朴,有失威仪”之类的话,顺从地放下了翼善冠,去拿那件常服。只是心里那份疑惑,却如同投入水中的石子,涟漪不断扩大:皇上…好像真的不一样了。
在几个小太监无声而高效的伺候下,崇祯穿上了那件沉重的常服(真他妈沉!这金线怕不是有二十斤!)。他尽量挺首了依旧有些虚弱的腰背,走向那面巨大的西洋水银穿衣镜。
镜子里映出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略带稚气的少年。十六七岁的年纪,轮廓清秀,但眉眼间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深刻焦虑和疲惫,此刻更添了几分大病初愈的青白和一丝…几乎被焦虑掩盖的“新奇”茫然。
这就是崇祯…是我了。
他盯着那双眼睛,努力传达着自己的意志:听着,朱由检!焦虑退散!恐惧滚蛋!新手上路,不懂就问!活着,懂吗?活着就是胜利!
然而,眼神深处,那属于亡国之君的阴影,如同煤山冰冷的雾霭,似乎从未真正散去,只是在刚刚燃起的求生意志下暂时蛰伏。
“皇上,”王承恩的声音适时响起,带着十二万分的小心翼翼,“温大人、杨大人等,己在乾清宫暖阁候驾。您看……?”
暖阁?那就是见大臣的地方。第一次正式见面…是摊牌?安抚?还是被架空?
崇祯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残留的那股奇特的安神香气似乎失去了作用。胃里又开始隐隐抽痛,脖子上的幻痛也仿佛若隐若现。
煤山的阴影,好像随着王承恩那句“候驾”,瞬间从蛰伏中抬起头,无声而冰冷地狞笑着逼近了一步。
他抬起似乎有千斤重的手,喉咙发紧,感觉下一秒自己就要吐出来,或者尖叫着跑掉,却最终只是从牙缝里挤出一个沙哑的音节:
“…带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