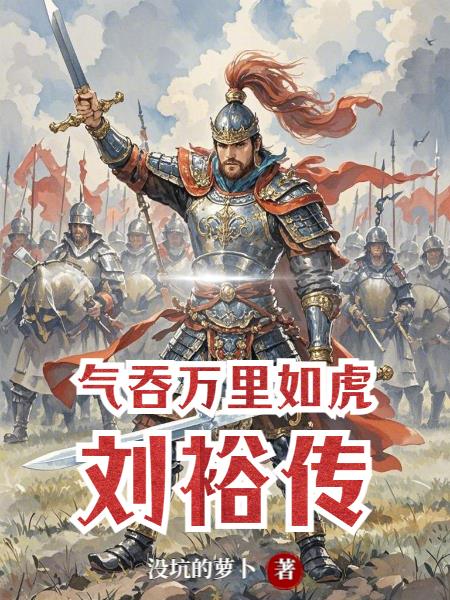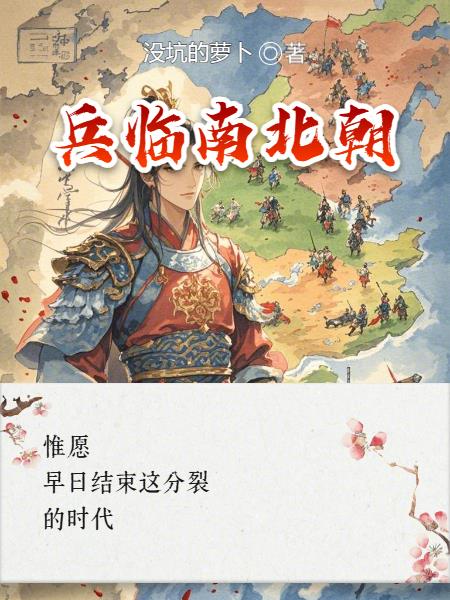第1章 丹徒田垄
东晋兴宁元年(363年)三月,暴雨如倾。
雨鞭抽打着京口丹徒县的茅草屋顶,破洞处漏下的水在泥地上汇成浑浊的溪流。刘翘一脚深一脚浅地踹开柴门,蓑衣上的雨水泼溅在墙角堆放的农具上,铁锄和木耒的阴影在油灯昏黄的光里狰狞晃动。
“稳婆来了!”他喘着粗气,将一个浑身湿透的老妇人推进里屋。老妇人顾不得拧干衣摆,急急扑向土炕。炕上,赵安宗蜷缩在薄薄的麻絮被里,面色惨白如纸,汗水和泪水糊了满脸,每一次宫缩的剧痛都让她喉间发出野兽般的呜咽,指甲深深抠进身下发黑的稻草垫。
屋角阴影里,刘翘的母亲、彭城刘氏这一支如今最年长的妇人,蜷在吱呀作响的藤椅中,枯瘦的手指神经质地捻着一串磨得发亮的桃核念珠,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炕上挣扎的儿媳,嘴里反复念叨着,声音嘶哑,带着浓重的彭城口音:“作孽啊…彭城刘氏,高祖苗裔,落到这步田地!你爹那点俸禄,连口稠粥都喝不热乎!这日子,比佃户都不如!”
油灯被穿堂风吹得忽明忽灭,墙上的人影也跟着扭曲晃动。接生婆赵媪跪在炕沿,粗糙的手在赵安宗高隆的肚腹上用力推按,嘴里念念有词。突然,她动作一顿,借着昏暗的光线,目光死死黏在新生儿刚刚娩出、还沾满血污和胎脂的小脚丫上。那小小的脚掌心,赫然缀着七颗殷红如血的痣点,排布竟似北斗!
“老天爷!”赵媪倒抽一口凉气,声音都变了调,“脚掌七星!这可是……”
“住口!”一声低吼如炸雷般响起。刘翘不知何时己站在门边,脸色铁青,蓑衣上的雨水还在不断滴落,在他脚边积起一小滩水洼。他一步跨到炕前,高大的身影带着一股湿冷的寒气,几乎将油灯的光完全挡住。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凶狠地瞪着赵媪,声音压得极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狠厉:“管好你的嘴!这等话传出去,是想招祸吗?想让我们一家子都不得好死?!”他喘着粗气,目光扫过墙角堆着的破旧犁铧、缺口的镰刀,还有窗台上那个积满灰尘、药渣早己干涸的瓦罐——那是去年赵安宗病重时赊来的药,至今没还清药钱。屋顶的漏雨滴滴答答,像敲在人心上。
赵媪被他眼中那股近乎疯狂的戾气慑住,浑身一哆嗦,剩下的话生生咽了回去,再不敢看那婴儿的脚掌,只埋头继续忙碌,嘴里含糊地应着:“是…是…老身多嘴,多嘴了…”
屋外的暴雨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哗啦啦冲刷着破败的茅屋,冲刷着丹徒这片贫瘠的土地。**门阀如天堑,高悬于九霄。王与马,共天下**的余音在建康的朱门玉户间回响,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子弟,乌衣巷里诗酒风流,清谈玄理,视这江北烽烟、流民哀鸿如尘芥。而在这京口,扼守大江南北的咽喉之地,在那些世家高门眼中,不过是屯聚流民、蓄养北府精兵的“北府”所在。寒门庶族、流离失所的北来侨民、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的土著农户,如野草般在这片饱浸血汗的土地上挣扎求生。
“哇——!”一声嘹亮到几乎撕裂雨幕的啼哭,猛地刺破了茅屋里的压抑和死寂。这哭声带着新生命不顾一切的蛮横,竟暂时压过了屋外滂沱的雨声。一个浑身通红、皱巴巴的小生命,在祖母绝望的祈祷、接生婆惊惧的沉默和父亲焦灼而凶狠的注视中,降临在这风雨飘摇的乱世,降临在这丹徒田垄间最卑微的角落。他的小脚丫,那七颗殷红的痣点,在昏暗摇曳的油灯光下,像一串沉默燃烧的血色星辰。
刘翘紧绷的身体终于晃了一下,他慢慢走到炕边,伸出手,带着厚茧的手指极其轻微地碰了碰婴儿温热的小脸。那指尖带着雨水的冰凉和泥土的气息。窗外,一道惨白的闪电撕裂墨黑的夜空,瞬间照亮了屋内每一张脸——赵安宗虚脱的苍白,刘母刻满苦难的皱纹,赵媪残留的惊悸,还有刘翘眼中那复杂难辨、混杂着疲惫、凶狠与一丝渺茫微光的眼神。紧接着,滚滚惊雷炸响,仿佛要将这摇摇欲坠的茅屋彻底震碎。